
发布时间:2025-06-19 浏览量:人次
本文要讲述的是丧葬仪式发生在一个不幸家庭的真实故事。
家庭成员四口:母亲、父亲、姐姐、弟弟。
母亲两年前因病去世,弟弟从小呆傻,姐姐石梅本在浙江打工,却突然接到父亲石营车祸身亡的噩耗。村落中,除了远房的几个叔伯,此家再无亲人,姐姐也不过25岁,还未成家,在经历了母亲的病、死、葬之后,又要独自面对父亲的死和葬。自从获知这一家的男主人飞来横祸,石梅赶回之前,就有邻居自发前来帮忙。但整个丧事如何操办,拿主意的只能是石梅。在综合思量了邻人、叔伯们的建议及自家状况后,石梅请来了掌坛师(掌坛师是丧葬仪式中请来做法事的道士们的头头),决定以两天两夜的打绕棺形式举行父亲的葬礼。
在当地的风俗中,正常的死亡一般指60以上的老人,正常病逝或无疾而终;非正常死亡叫“凶死”,主要从死因上作判别,他杀、车祸、自杀、溺水、火灾、难产等意外而亡者,皆属非正常死亡。
正常死亡的丧礼活动采取打绕棺的方式,绕棺有大小之分。大绕棺一般两天两夜或三天三夜,小绕棺只需一天一夜。大绕棺通常请六七个道士,小绕棺请四五个道士。
非正常死亡的丧礼活动须打道场。打道场仪式烦琐,传统时期一般要七天七夜,请道士十三四个,现在大多简化到三天三夜,请七八个道士。打道场包含了打绕棺的大部分内容,但多出了芜杂的替死者改罪的法事。
因此,按照当地的丧葬习俗,石营的死属于“凶死”,须打道场改罪,然而石梅却不这样认为,事实上这跟同族远房叔伯的意见不同,但石梅的决定并未招致行动上的反对和阻碍。
一方面,打道场的花费相对较大,虽有传言说石梅在外赚了一些钱,但她选择从简办理父亲的葬礼也情有可原,毕竟,石梅母亲不久前的病逝刚给这个家庭的经济以重创。
另一方面,社会的发展使得村庄内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村民间“核心家庭本位”的观念越来越重,很少有人再愿意出于某种公共的目的站出来去管别人家的私事。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的风俗可以被任意篡改。石营毕竟是出车祸死的,无论从简与否,葬礼都应该突出这是一场非正常死亡者的葬礼。
对于一个非道士从业者和旁观者村民而言,最直观的为非正常死亡者改罪的仪式无非三个:破地狱、上刀山和下火海。上刀山、下火海需要的时间很长,两天两夜的绕棺肯定是没办法做的,但紧凑点,第二天下午或晚上破个地狱还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
但石营的葬礼,尸体马上要上山了,道士也没有要破地狱的意思。在终于意识到死者就要这样入土为安时,石梅的远房叔伯石洪带着几个石姓族人找到了石梅。
他们认为,对于一场非正常死亡者的葬礼而言,念再多的经、拜再多的忏也是不够的,怎么也要破破地狱、上个刀山、下个火海,实在不行,只破个地狱也算将就。一个都不做,无论怎样都是说不过去的。不破地狱,石营的魂魄就没办法转世投胎,不投胎,石营的魂魄就会转而变成厉鬼在村庄游荡。这肯定会对村庄中生活着的人产生莫大的影响。说不定哪天,变为厉鬼的石营的魂魄就会缠住某人,那时这人离死也就不远了。石营的魂魄不投胎,石营就永远没办法入神榜,也就永远不可能被列为祖先神来供奉。总之,他们认为,破个地狱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
虽然只有25岁,但已经在外打工整10年的石梅面对叔伯们的质疑表现出的却多是淡漠。
她认为,车祸并不是父亲的错,也不是父亲的罪,车祸去世了就要下地狱的说法也是荒谬的。这世上有地狱吗?她反问她的叔伯。多诵诵经、拜拜忏就可以了,两天两夜的打绕棺哪容得下那么多改罪的仪式。
石洪等人最终并未说动石梅,相反倒是被石梅反驳得哑口无言。但他们依然坚持认为,破地狱是必要且必须的,他们还认为,石梅这样做有故意的嫌疑,但他们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得转去找掌坛师。
掌坛师声称仪式过程是遵照主人家的吩咐进行的。他们也只能按照主人家的要求开坛作法。但石洪们反问,死得不好总要破个地狱吧?掌坛师无言作答。
石洪将掌坛师拉到一边,递了烟,又一阵窃窃私语。之后,掌坛师在停放棺材的棚子旁边画了一个小地狱,五方放上了瓦片,他吹起海螺,举行了一场短暂的破小地狱的仪式。五方瓦片最终被锡杖打碎,石梅看到了,并没有制止。
这时,天行将破晓,而上山仪式务必要在鸡鸣前完成。道士们没有休息(按照惯例,一场法事完了,无论大小,道士们都会歇上一段时间。),掌坛师又匆匆吹起海螺,举行了上山的仪式。
对这次丧葬仪式冲突中行动逻辑的分析
远房叔伯与石梅的冲突相对于漫长的葬礼只一晃而过,冲突何来?冲突反映了什么?
石梅虽然是村落年轻的成员,但常年在外务工的经历给她带来的肯定不仅仅是工资和年终奖金。按照她的说法,车祸并不是父亲的错,也不是父亲的罪,地狱有没有都要另说,车祸去世了下地狱的说法更是荒唐的,这话当然是正确的,但这话却潜在地否定了村庄地方观念中针对死因的道德批判。
人都是生活在一定场域中的,也是被场域形塑的。十年沿海地区的打工生活,十年与现代知识话语的耳鬓厮磨,石梅观念的改变完全可能是内外兼至的。
因父亲的意外去世回到村庄的石梅,作为故土的异乡人,头脑中早已淡去的传统乡村社会关联的逻辑无法重新启动并运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基于这样的分析,丧葬仪式过程中石梅与远房叔伯们的短暂冲突凸显的是外来经验、规律与村庄地方逻辑之间的某种角逐与博弈。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科学知识和理性话语早已取代了包括民间信仰在内的传统文化而居于社会精神生活的中心,现代性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权威使其不断地改变着乡村民间社会的精神文化结构,促成以现代性和国家意识形态为底蕴的大文化对以地方性知识为底蕴的小文化的挤压和冲击,在这样一种背景和语境下,依死因的不同对葬礼仪式作简单分类的地方逻辑受到了外来眼光的挑剔和质疑,于是,石营葬礼上的冲突发生了。
然而,丧葬仪式结束后的一次深入调查却提供了冲突分析的另一种可能性。
在笔者与石洪的访谈中,他说到了为什么他认为石梅是个不孝女,为什么石梅对父亲葬礼仪式的某些安排是故意的。
石洪说:“她跟她爸石营和不来。到底是为啥子我也不咋清楚。只是在石营出事前听她说过几句,自从***得病过世后,她就很少跟她爸说话,在外也不咋打电话回来。这女娃子对她爸有怨言。她爸死得不好,她也不想多给她爸改罪,她还在跟她爸怄气。石营以前对***不好,她这是替***出气哩。要说她接受了新观念,她咋不把石营拉去火化了。***死得也不好,葬礼还不是打了道场。偏偏到了石营这里,她倒认为没有罪要改,她爸难道比***的罪孽轻?我也不想为难这个苦命的娃儿,葬礼上我上的钱是最多的。我知道她苦,她弟弟又是那个样儿,但再苦也没必要跟死人置气嘛,是不是?就按照传统、依着黄历把死人送到那边就完了,打道场变成打绕棺了,我也不咋好说的,但都不给死人破地狱,不帮死人减罪、改罪,这就说不过去了嘛。”
在与石梅的其他族人及邻居的交谈中,乡人们也或多或少提到并认可了石洪的看法。
石梅的一个远房堂叔向笔者解释了他跟着石洪去找石梅磋商、理论的理由,他认为葬礼是石营的葬礼,石营是村庄里的一员,石营肯定希望自己的葬礼按照以往的传统来办,即使石梅对村庄处理死亡的方式心存异议,她也应该顺从死者的意愿,因为葬礼最终是为了死者而办的。
石梅的一个邻居认为,按说,葬礼怎么办都是主人家自己的事,跟别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以前也不是没有因为穷只给死者开个路就上山埋了的情况,但石梅把她爸本该打道场的葬礼改为了打绕棺,就有说不过去的地方。***死得也不好,虽然没像老辈那样闹上七天七夜,但三天三夜的葬礼也是破了地狱的。一样的父母,两样的待遇,这样就不好。何况,石梅虽是个苦命的女娃,但她脑瓜还是灵的,会赚钱。她在浙江跟别人合伙办了个小厂,招了几个同乡的年轻人给她打工,她们专门接大厂不愿干的零碎加工活,她家女娃就跟着石梅做事。要说缺这个打道场的钱,好像也是不应该的。
但访谈中也有一些人并未注意到石营的葬礼与一般葬礼的区别,他们将关注点主要放在了石梅的冷峻以及葬礼中石梅傻弟弟不合时宜的举止上。在被问及是否真的认为没有经过恰当的改罪仪式超度的“凶死”之人很难转世投胎时,有人相信,也有人认为这仅是种说辞,是村落的习俗,大家都按照这样的方式处理死亡,也就成规约了。
葬礼结束后,石梅带着弟弟很快离开村庄,回到了打工的浙江绍兴。
几个月后,石梅回村为自己扩充的小厂招人,为了求证乡人的说法、理顺石梅在父亲葬礼上的行动逻辑,笔者在接到村人的告知后,又一次回到村里并对石梅进行了访谈。
石梅招工的对象主要是准备或刚刚在镇中学辍学的学生,或许是因为笔者比较真诚的缘故,石梅对笔者的提问并未过多反感,但采访也远非令人满意。直到笔者离开,石梅都不愿意谈论自己家里的恩怨与是非。不过,石梅承认,她内心确实积攒了不少对父亲的怨言,而对于按照死因区分仪式方式的葬礼观念,她虽然不赞成,但也不反对,不过,她并未直接做出解释。
至此,综合所有访谈资料及自己的参与观察实践,笔者认为,葬礼上,石梅将打道场改为打绕棺,并删减了破地狱等冗长的改罪仪式,更可能的原因不是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而是如石洪等人所说的她与父亲之间的恩怨纠葛。
按照母亲的葬礼规格举办父亲的葬礼,葬礼也只不过多延长一天一夜,多做几场法事,这并不会增加太多的花费(大概多花四五千元左右)。即使石梅手头的钱正紧,只要她愿意去借,她的远房叔伯也不会坐视不理。也就是说,从某种程度上讲,父亲葬礼上石梅的表现确实有赌气和故意的成分。
在石梅的心目中,母亲和父亲的位置、分量是不一样的,当父亲葬礼的筹划权不得不交至她手上时,与父母心理距离的这种落差很有可能会通过对父亲葬礼的某些具体安排体现出来。在这样的事实与情形下,石梅的行动逻辑须做出重新地解读。对于丧葬仪式中的观念,石梅是持怀疑态度的。正是因为怀疑以及怀疑背后的反问,她才能在与叔伯们的争论中占据上风。然而怀疑与反问并不足以反驳以传统观念为结构基础的丧葬仪式传统本身。
对于石梅以及村里的乡民来说,观念体系是分层的。浅层观念容易认知、判断,同时也易嬗变。而深层观念,比如对死亡的认知,是模糊和游移的,甚至因无力思考,深层观念是被搁置、放任的。也因此,这些模糊和搁置决定了与之相伴的仪式结构的牢固和稳定。只不过在这个案例中,冲突双方对仪式结构牢固程度的认知存在着差异。
换句话说,石梅不赞成的葬礼观念,但对丧葬仪式传统,她是认同的。也正因这认同,石梅行为中的赌气和故意的成分、区别对待父亲和母亲葬礼的意图才变得合乎情理。
同样,石洪等人也不一定真的认为不经过改罪,死者的魂魄就只能变成厉鬼到处游荡,但身处村落文化网络中,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扮演了地方传统的维护者。
葬礼上的短暂冲突,并不过多地体现着外来文化与地方逻辑的对立,而最主要反映的则是对于传统的利用与反利用。“尽管相当多的村民实际上已经逐步接受了现代性的知识体系,并且相信它所体现出来的意识形态至上性与权威性,但他们可能去顺应传统而非反叛传统,尤其是在涉及与人类生存意义有关的非世俗化的事件与仪式中,情况就可能更是这样。”传统仪式结构本身具有的吸附性、发散性以及人们在长期生活中对传统的依赖与借用,使得传统在没有行政强制力量压制的环境下能够自为存续。
当然,随着人口的频繁流动,村民的本体性价值认同确有变化,这变化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农民社会性价值追求上的变化。具体到丧葬活动而言,据笔者的观察,村民社会性价值追求上的变化,主要体现在部分正常死亡者的葬礼上。关于死亡正常与否的判断,事实上是个社会性的评价。正常死亡者,死者家人与周围村民的认知一致,正因为这一致,周围村民反倒宽容起来。有些有钱人家迎合社会观念的变化,在为正常死亡的亲人举行葬礼时,除保留了主要的传统仪式和法事外,另请了城里的乐队助兴。对此,村民们没有任何责难,反倒觉得死者的儿女们孝顺、死者死得有面子。
对于石梅来说,传统丧葬仪式方式也依然是她处理父亲死亡的唯一方式,甚至也是她对“如何死”的唯一想象。正是因为这唯一,正是因为可以预测,无论她相不相信死得不好会不会下地狱,无论她的父亲以及村庄里的其他人相不相信死得不好会不会下地狱,破地狱的仪式,对于父亲而言,都将是重要的。
她反对为父亲举行破地狱的仪式,并不主要是在反对破地狱这一仪式,这从她对掌坛师在叔伯们的压力下不得不匆匆完成的破小地狱仪式的默认上便可见一斑。
(文中出现的人名均为化名)
(全文完)
特别提示:本站所标注价格及相关信息来源于网络采集,仅供参考,实际情况以墓园前台咨询为准。

墓地价格:13800元(仅供参考)(点击询价)

墓地价格:19800元(仅供参考)(点击询价)

墓地价格:15800元(仅供参考)(点击询价)
墓地价格:壁葬8000元、墓地11800元(仅供参考)(点击询价)

墓地价格:19800元(仅供参考)(点击询价)

墓地价格:16800元(仅供参考)(点击询价)

墓地价格:12000元(仅供参考)(点击询价)

墓地价格:15000元(仅供参考)(点击询价)

墓地价格:5000元(仅供参考)(点击询价)

墓地价格:21000元(仅供参考)(点击询价)

墓地价格:15000元(仅供参考)(点击询价)

墓地价格:(仅供参考)(点击询价)

墓地价格:26800元(仅供参考)(点击询价)
墓地价格:23800元(仅供参考)(点击询价)

墓地价格:(仅供参考)(点击询价)

墓地价格:格位10800元,墓地59000元(仅供参考)(点击询价)

墓地价格:18900元(仅供参考)(点击询价)

墓地价格:15000元(仅供参考)(点击询价)

墓地价格:16800元(仅供参考)(点击询价)

墓地价格:28000元(仅供参考)(点击询价)

墓地价格:(仅供参考)(点击询价)

墓地价格:30500元(仅供参考)(点击询价)

墓地价格:12800元(仅供参考)(点击询价)

墓地价格:18900元(仅供参考)(点击询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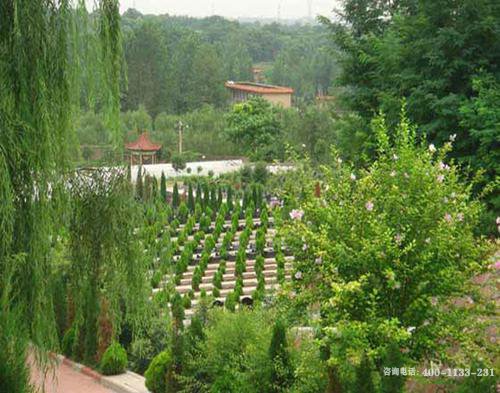
墓地价格:20000元(仅供参考)(点击询价)

墓地价格:8900元(仅供参考)(点击询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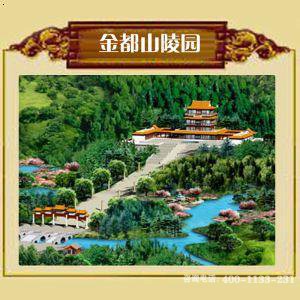
墓地价格:29800元(仅供参考)(点击询价)

墓地价格:29800元(仅供参考)(点击询价)
